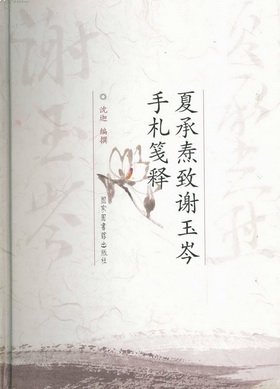
沈迦编撰《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》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。16开精装一册。420页。
本书收录夏承焘(1900-1986)致谢玉岑(1899-1935)书信六十二封,另有夏承焘致钱名山四封,致郑曼青、顾颉刚、胡小石、刘节、容庚、张孟劬、钱仲联各一封,共计七十三封。时间从1927至1935年。此批信札原为钱名山之孙、谢玉岑外甥、诗词学者钱璱之先生所藏的劫后之物,钱先生曾以此批信札写有数篇有关的文章,并作过部分信札的注释。沈迦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,发现谢玉岑曾经到过温州的浙江第十中学执教过一年,时间1925年秋至1926年夏。浙江第十中学即现在的温州中学,亦是沈迦的母校。在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朱自清、夏承焘、马孟容、夏鼐、陈叔平等名家皆曾先后在该校任教。但有关谢玉岑在该校任教的文字资料极少。后来沈迦通过网络有幸认识了谢玉岑长孙、谢伯子画廊主持人谢建新先生,知道有一批夏承焘致谢玉岑的书信存世。谢建新就将这批书札一一拍摄照片并刻录成光盘,再加钱璱之先生的注释手稿复印件,一起寄给了沈迦。
在此基础上,沈迦用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间,将这批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一一进行了笺释,大约是用一星期时间笺释一封。我们今天所读到的《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》,除全部信札影印外,还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文字内容:“时间”:即信札的时间,有些写明时间,有些则没有,就通过其他的资料进行考定其公历时间。“署款”:原信札上写明的阴历时间。“用笺”:信札所用的纸质情况。比如红格八行笺、便笺、公用信笺、普通宣纸等。“夏记”:即夏承焘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等其他文字中是否有此信件的记载。“钱记”:即在钱璱之先生注释文稿中是否有此信件的记录。“今按”:是沈迦对此信件的文字考证。它包括该信件写作的时间背景等有关内容。“释文”:信件的释文、短句、标点。“注释”:关于信件中所涉及的人物、书籍、文字等进行注释。
对古人、前人的信札、手稿和书法墨迹等进行笺注,最大的难度是原稿的文字释读。夏承焘在信札里时常喜用古今字、异体字、通假字,而且多为行草书体,所以要一字无误地予以辨读的难度极大。沈迦有时为了一个字,会与爱好书法的朋友在QQ里聊上半天。其间,也为了几个字专程去常州,向钱璱之先生当面请教。沈迦在《后记》中曾经写道:“字算认出来了,但句子读不懂;句子读懂了,用典还不明白。这是我第一次点校古籍,也是从头开始学的过程。事非经过不知难,我终于明白,笺释古文的难度并不亚于翻译英文。”但他幸运地得到了许多益友们的帮助,疑难问题大多得到了解决。我曾在读书中信札影印件的同时,再与沈迦的“释文”做一一比对,几无错字或误字。使我这个自认为鉴阅过无数古今书法墨迹的人来说,也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。因为有许多疑难字,我不仅不认识,而且连“猜”都“猜”不出来。另在“释文”的断句、标点、分段等方面,几无明显“瑕疵”。
在本书的第五封和第九封信札中两次提及的况周颐《阮庵笔记》一书,沈迦在“注释”中没有笺释出来。此书我有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影印本,所用版本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藏书。《阮庵笔记》又名《阮庵笔记五种》,晚清著名金石收藏家、两江总督端方(匋斋)题写书名,光绪丁未年(1907)刻于白门(即金陵)。应是木活字本。书中有《选巷丛谈》二卷、《卤底丛谈》、《兰云菱梦楼笔记》、《玉梅后词》,有许多清人诗词、古金石器物、碑帖目录等内容。此书在况周颐的诸种笔记中并不著名,然当年印本甚少。
夏承焘致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三件手札的内容,可以将之大致分为以下几大类:一是夏、谢两人关于词学研究、诗词创作的交流与探讨,包括借阅词学书籍等。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。其次是双方珍重友情,珍惜人才,提携道引。其三是夏、谢两人各自求对方的书画,以及夏代谢向其他学人求书法墨迹。信札中涉及到的当年词学同道有:朱彊村、吴梅、吴昌绶、任二北、龙榆生、周梦坡、唐玉虬、蔡松筠、叶恭绰、唐圭璋等人,而书画家、学者等更是难以详计。通过阅读这批信札,使我们了解到在民国年间,一批远离“新文化”运动的文人、学者和书画家们真实的生活状态,另有他们重友情,重承诺,相知相惜等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,以及当年词学界的一些学术情况。古人云: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寡闻。”据夏承焘日记可知,谢玉岑也先后写给其信札约有百余封,可惜今皆亡佚无存。
清人梁章矩《退庵随笔》中云:“凡朋友契阔之余,必借尺书以通情款。尝见有深交密契,一分手而音讯缺如者,非必其恝也。” 夏、谢两人虽然在温州相处仅仅只有一年,但后来却成为了真正的“深交密契”,亦师亦友。两人分别以后,鸿雁传书,几乎无话不谈。夏还曾请谢以清代常州诗人黄仲则的诗句“我近中年惜友生”篆刻一闲章。袁枚在《随园随笔》中云:“今师与弟子帖称友生。”可见夏视谢为其之“良师”。在夏承焘致谢玉岑的六十二封信札中,有许多是关于词学研究和填词方面的内容,因此方面极具专业性,故一般读者未必能解其中玄奥。但另有一些书画方面的内容,不妨当作艺林掌故阅读。
谢玉岑除在诗词上极具造诣外,还精擅书法,真隶行篆皆工。四体之中,隶篆尤佳,名重江南,故夏承焘在信件中亦时常向其求书。谢玉岑曾以贫鬻书,并定有润例,且请人画有《青山草堂鬻书图》,附润例于后。实除部分收取润例外,多为贻赠友朋。从夏承焘致谢玉岑信札中知,夏先后得到谢的横幅、篆书长联、金文小幅等书法和画作,另还通过谢向钱名山、张大千、郑曼青、谢月眉等人代求书画。谢玉岑也向夏承焘求书法作品和题跋。后谢玉岑在病中时,曾四方求文人学者书扇,以此消遣病中时光,他遂请夏承焘为之推荐。在夏承焘致谢玉岑书札中有写给顾颉刚、胡小石、刘节、容庚、张孟劬五人的信札,就是求书扇推荐信。但谢玉岑收到后因病革而未能寄出而遗留了下来。前辈风雅,令人神往。
夏承焘在1935年4月15日致谢玉岑信中有云:“此间马一浮字极佳,弟嫌其人有习气,不去求,杭州学人书家皆少有。郁达夫虽弟之同事,字不成字,可不必耳。”夏承焘当时任教于杭州的之江大学,但郁达夫只有在之江大学“预科”读书半年的履历(1912年),并未有在该校任教的记录。故“郁达夫虽弟之同事”不知何指?郁达夫曾任杭州作者协会理事,难道夏承焘也曾在此协会中兼职?在此存疑待考。
除信札的原稿之外,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人和前人的信札(尺牍)文字,其实大多有增删润饰之嫌疑,所以它们的真实性就大打了折扣。有文字阅读的愉悦感而少有文献的参考价值。郑逸梅先生在《尺牍丛话》一书中尝云:“书札之可留者凡三,一重其人,二重其字,三重其文,否则无取也。”夏承焘致谢玉岑等人的七十三件手札,可谓“三重”俱备,故弥足珍贵。我在此要真心感谢钱璱之先生和沈迦先生,以及其他许多的热心人士,为这批信札的整理、笺释、考订和出版所付出的心血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,其实就是这种不让其澌灭、并将之延续和传承的历史,这也正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精神内涵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