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a.jpg)
s.jpg)
原文见《万象》1942年第8期12页。
陈蝶衣,原名陈元栋,笔名狄薏、陈式、陈涤夷、玉鸳生、方忭,江苏常州武进人,中国著名出版家、作家、填词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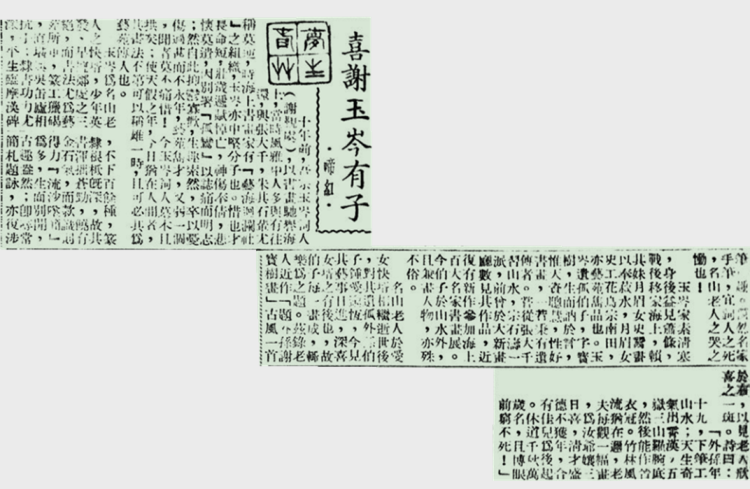
十年前,吾宗玉岑词人(谢觐虞),以书画驰誉于海上,当时风雅中人多与有往来,与张大千、朱其石辈尤称莫逆,时海上书画家有“艺海迴澜社”之组织,玉岑亦中坚分子也。惜也才长命短,壮岁递赋悼亡,神伤奉倩,悲怀莫谴,因别署“孤鸾”以志痛而明志,然自此郁郁寡欢,生趣索然,卒以忧伤过甚而不永年,艺苑奇才,又弱一涸,闻者莫不痛惜!今玉岑词人墓木且拱矣,使天假之年,今日犹在人间者,其书法不第可以称雄一时,且可必其为艺苑传人也。
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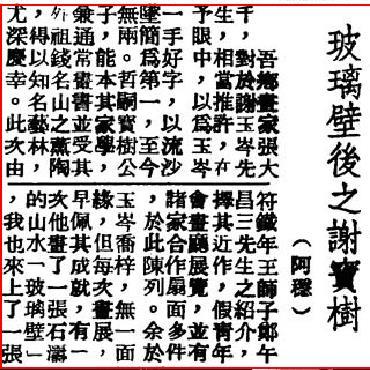

.吾乡画家张大千,对于谢玉岑先生,相当推许,在予眼中,以为玉岑一手好字,以流沙坠简为第一,至今无两。哲嗣宝树公子,能本其家学,兼通常书画并受其外祖钱名山之熏陶,得以知名艺林,尤深庆幸。此次由符铁年王师子郑午昌之绍介,择其近作,假青年会画厅展览,并有诸家合作扇面多见,于此陈列。余于玉岑乔梓,无一面缘,但每次画展,早佩其成就,有一次他画了一张石涛的山水[玻璃壁],我也来上了一张,后皆售出,但是价值高低,我却退避了三舍,可见他是作家当中的后来居上的一位,值得佩服。再者今年写稿子,尚属第一次,写捧场稿子,是一篇半篇,都不会写过的,否则同文看见,一定说我为何不捧“破记录”的人?
按:本文摘自 1944年5月14日《社会日报》[0003 版]。
..
.jpg)
谢伯子画展趣事-聋哑青年群就笔谈(冰心)
青年画家谢伯子君,为钱名山外孙,故谢玉岑词人之公子。少时从其父执张大千郑午昌氏学山水,出笔便已不凡。年来潜心研讨,益复精进。今方展其近作于八仙桥青年会画厅(十一日至十七日)为期七天。出品约百帧,携名书家合作扇面两百页,三日来参观者极形踊跃,无不惊其能事,叹为天才。所作已定去十分之九,情况热烈,为青年画厅历来画展所未有。尤奇者,本市聋哑青年,争欲一见谢君庐山真面,不期而集者多人,一时伸纸笔谈指手画脚,大有应接不暇之势。古人云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”。伯子既患聋哑,自无应务烦其心曲,故能宁静专一,发挥智慧,反收事半功倍之效。获此优绩,绝非偶然,其未来成就,则尤未可限量也。(附图为谢君近作山水精品)
按:本文摘自1944年5月16日《海报》。